

湾区设计学院(筹)坐落在满京华国际艺展中心的设计别院,建筑面积约 2 万多平方米,位于深圳宝安区。2018 年,中国现代教育界泰斗王受之教授应邀作为院长,主导湾区设计学院创建工作,打造着眼国家利益和国际视野的高端学术平台。
同时,王受之先生也发起《湾区设计论坛》,将陆续邀约学术和文化界、产业与设计界、当代艺术与文博界中最具代表性的杰出人物,围绕当代艺术、设计教育、生活美学、社会热点等诸领域,展开系列主题对话,探讨设计与艺术的未来,带来最前沿的思考。
10月21日下午,在满京华·艺展中心一楼,由湾区设计学院(筹)主办,中国现代设计教育界泰斗王受之先生主持,满京华教育设计出品的湾区设计论坛今天在满京华艺展中心首次亮相。湾区设计论坛是满京华集团倾力打造的满京华公开课系列活动之一,本次公开课的主题是听南王北柳共话湾区设计。
本篇为王受之先生与柳冠中先生的对谈部分全记录,欢迎各位转发、收藏,相信一定获益良多。

王受之:
所以今天我和柳老师讲话,我跟他商量了一下,第一段还是从我们的历史讲起,就是我们怎么学设计的,我们对外国设计有什么感触,这一段资料录下来,也是将来我们的口述历史的组成部分,当然后面一定会讲到我们对现代设计教育的问题、意见和看法。
柳老师,请问您是哪一年去德国留学?在什么地方留学,跟随哪个老师,学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让你最震撼?
柳冠中:
这一段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我是1981年,当时在工艺美院读研究生,从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回到工艺美院,因为当时工艺美院文革以后要招生,缺师资,要我回去,建筑设计院不放,因为我是学室内设计的,学校就想办法招研究生,在学校读了两年研究生,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正好派我到德国去,是作为访问学者去的,当时访问学者是两年,后来延长一年,在德国待了三年。
王受之:这是1981年?
柳冠中:
1981年4月份。当时出去学了三个月的德语,就进入斯图加特的艺术与装饰学院,印象十分清楚。到了德国就是到处看,根本没思考,后来才慢慢回过头来,回到学校成立工业设计系,要组系了,如果回来当一个老师,可能跟现在的我完全不一样。因为回来就要当系主任,思考的问题就不是上好一门课的问题了,就要思考这个专业怎么搞,所以这才回头看我在德国经历的事情,才看出它的作用和意义,所以现在我的看法是,咱们出国的人很多,光看是不解决问题的,你看到的东西和事实是不一样的。
我现在做报告不是经常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吗?眼见不为实,眼睛看到的背后的东西才是真正要沉淀的东西。我们国家改革开放40年,我们眼见了很多东西,眼见背后怎么样?现在要转型,这就是在思考了,也许是在某种程度里有理论的重要性。咱们在座的都学过画画,在没有学过色彩知识的时候,你去写生,顶多是深绿、浅绿、深黄、浅黄,学了色彩知识之后,你马上就知道其它的颜色,在没学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到,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我当时在德国斯图加特,这是一个汽车城,当时我第一次参观,我就觉得非常震撼,也很奇怪,为什么这里每个办公室都有黄种人。我当时以为中国人真了不得,当时每一个流水线的工位上也有黄种人,我说中国人真了不起,我们是第一批出来的,居然有这么多人出来了,但是仔细一问,了解到他们是日本丰田的人。
这就值得我们思考了,为什么强调这个?咱们现在仍然还是一个小生产意识,都强调个人。丰田一年派100人,形成团队过去的,有高级工程师、一般工程师、车间管理人员,也有操作工,他们做了三年计划,你说这三年300人回去干什么?他绝对不只是几个技术,几个技巧的掌握,它是带着一个结构回去的,所以丰田后来一下子就发展起来了,当时没想这么多。1984年回来之后,1987年再过去,我发现那些工厂里怎么还有黄种人,后来了解到是韩国现代的人。我们中国现在还没有派这样一些基层的员工,我们派出去的都是研究人员、教授。
现在中国的设计专业成天讲元素、技巧、知识,这是我们目前最值得思考的,我们国家从晚清开始就派留学生,都是个人,到现在仍然是个人。
王受之:精英。
柳冠中:
都是精英,人家是梯队,是系统,是整体,是结构,是机制。所以在我们国家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我们总崇尚十年寒窗苦,考上状元,娶一个皇帝的女儿,一步登天,都想着自己升官发财,忘掉了一个社会的整体,这也是我们设计教育目前面临的深层次的问题。

王受之:
您作为一个访问学者进入了斯图加特这个设计学院的课程,您觉得有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呢?因为你原来在中央工艺美院是上过四年本科的,现在到德国去读研究生,有什么东西让你记忆极为印象深刻的吗?
柳冠中:
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又是目前设计教育存在的问题,我当时去做访问学者,回来是要有所作为的,我就从一年级开始,就跟咱们一年级一样。
他们高中生毕业进到学校,都是高中生,他的知识或者水平都有限,他们的教授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教授就坐在讲桌上,没有像咱们端坐在那里,他们就跟学生聊天,聊半个钟头,你从哪儿来的,你喜欢什么,快下课的时候才说正题,布置一个作业,每个人到学期(一学期16周)结束的时候要设计一个鸡蛋盅。我当时就在想,要是我设计的话,两三天不就做出来了吗?对中国学生来说就不适应,但他们德国的学生,因为也是高中生,也不了解,教授要求下个礼拜碰头的时候,每个人拿出16周的工作计划。
他们上来就做计划,不是我们一下子钻到一个造型,一个材质,或者一个技术里面,他要把你的思路理清,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写论文破题,你怎么认识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引导学生从整体、系统地看一个东西,而不是从结果来看,重的是过程训练。
所以每一周教授会和学生谈一次,引导学生你该做什么工作,该做哪些事情。最后16周结束,每个学生面前一排鸡蛋盅,不是画的,有注塑的鸡蛋盅,吹塑的鸡蛋盅,玻璃的鸡蛋盅,钣金冲压、木头的、金属制造的、纸的鸡蛋盅。这个训练是整体的,我们现在讲程序、材料、人机学,根本没有这个课,每个礼拜有两个下午讲座,讲座就是讲这些,请的社会上的人来讲,学生听了讲座就在课题上落实,找他的解决方案,或者说结合它的课题。
到第二学期,又是一个16周的课题,设计小刀。因为鸡蛋盅只是一个材料,第二个课题就复杂了,复杂并不是本身复杂,一个是刀刃,一个是刀把,一个是跟人接触,一个是必须要跟被切割的东西接触。
王受之:两种材料。
柳冠中:
对,它要结合,它有材料过渡、人机过渡、结构过渡、工艺过渡,在这个小课题中,学生拿出来又是一排刀,剁肉的刀、剃骨头的刀、美工刀,工作用的刀。
第三学期让他们设计一个手电钻,最后每个人做一个手电钻出来,可以在墙上、木板上打洞,是真实的都要做出来的。7个学期,7个这样的课题,你想学生还要实习吗?到了工厂还需要重新学吗?不需要了,他学到了基本的流程,知识是自己找的。这是我回来之后的体会,现在认识到的,就是不灌输知识,你自己找知识,但是我给你提出目标,你在过程中把你所有学的技巧、知识都在用,不断地用,不断地熟练,永远不会忘,他也要素描,也有制图,也有材料学、人机学,都结合在这个项目里面,7次的重复训练,越来越复杂。
王受之:最后有多复杂,你能记得吗?
柳冠中:
最后就是一个太阳能的旅游船,从原理到做出船来,那些老师毕业设计的辅导只是点拨,从来不像中国的老师这么辛苦,他是调动学生的自学能力和扩展能力,这是他们大学强调的,不是强调技巧,技巧永远是为服务目标。
所以这回过头来联想我们对基础的认识,什么是基础?咱们的基础到现在还是中国传统的,“拳不离手、曲不离口”,都是技巧,而思想方法、扩展的思维能力没有学会。我的这一看法可能会得罪人,咱们毕业之后经常要回炉、进修,这是教育的失败,社会上这么多知识,还需要去培训?还需要到教室?你在大学四年,任何课程、任何作业都是训练能力的机会,不是为了100分,可是我们奔的都是100分,为了展览好看,所以现在咱们的设计院校,95%以上的学校的毕业设计展在国际上都可以拿奖,但是都是商业模型,都是手板,都是3D打印、CNC做的,你自己什么都没学到。
我们清华10年有一个本科生考上了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他最后的作业,也是一个学期下来,拿着作业进到展览厅了,他为了显示自己认真,他跟同学说,我这个模型花了100多英镑。让老师听见了,老师说,你今年的课白上了,明年重修,你什么都没有学到,你是3D打印的。而我们现在不都是3D打印吗,都是CNC吗,你真是自己做的吗?我们做设计的模型,绝对不是手板,那是商业模型,设计学的是过程中的模型,原理模型、结构模型、工艺模型、人机模型、心理学模型,或者是尺度模型、色彩模型。
为什么16周做一个设计?这个模型都做了,起码七八种模型,模型是设计师或者学生跟自己探讨的过程,是跟老师交流的过程,而不是给商家、给老百姓看的东西,我们全误会了,都要结果,展览很漂亮,然后贴个牌子“不许触摸”,那就是搞展览,只是给别人看的,背后没有支撑点。
王受之:
柳老师讲的这一段我很有体会,因为我在美国教书的那个学校,汽车设计系在美国算是数一数二的,那个学校叫做艺术中心设计学院,他们的汽车设计班有一个设计摩托车的,他们是14周要交一个作业,就是14周做一个摩托车,中国的摩托车设计是最后画出来一张图,打出来3D很好看,我们那个课最后打分是16个学生骑了16辆车到学校来打分,都是自己手工做的,我觉得那跟咱们的教学的差别非常大。
我们现在连边都还没有摸上,所以咱们不要整天说我们的设计教育达到国际水平,我跟柳老师同样的观点,连边都还没有摸上,别看这些热闹。


王受之:
下面我还是继续想问问柳老师,您在那边读书,我知道您有一个很好的教授叫雷曼教授,后来您也让他回国,我也见过他,这个雷曼教授对您的个人有多大的影响?
柳冠中:
说起我的老师,我觉得他值得我一辈子敬仰,一辈子学习。大家知道雷曼在国际上都是有名的,他不光到中国,他还到美国、阿根廷、古巴、印度尼西亚、台湾、日本都工作过,是一个国际性的教育家,他一直强调的就是方法引导。
他说他们系的构成是,这边是图书馆,那边是车间,学校里面学生没有自己的桌椅,三年级跟一年级共用一个教室,是交流用的,没有固定的位置,三年级的学生可以引导一年级,四年级跟二年级在一个教室,大家在里面聊聊天,放放书包。而每个车间里都有一个工位,就是你有一个想法,就到车间做。
我当时做那个鸡蛋盅,我在画,雷曼老师说,今天开始不许你画,你有想法就到车间去,你有想法就做出来,逼着我只能去做。所以后来我做的设计,都是在过程中想出来的方案,不是画出来的。工艺有问题的,我解决工艺问题,材料有问题的,我解决材料问题,使用不方便,就从使用角度考虑。
再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那里的教授,像我们这样的规模,中国的教师起码有十几二十个,他们那个系里面每年进来二十个学生,教师只有两个,所以老师不可能给你上那么多课,都是靠兼职,他只是引导,做一个总监,过程都是别的知识结构补充。
所以我离开德国的时候,老师请我吃饭,他讲了这么一个游戏,这个故事我不知道讲了多少遍了。他说在欧洲有这么一个游戏,在足球场这么大的空间,随便扔一根针,让人来找针,看不同的人用什么方法,就看出学生的能力。
王受之:这个很难。
柳冠中:
旁边还搁了一桌吃的、喝的,他当时打比方,找典型人。他说第一个进来的是英国人,英国人比较规矩,比较保守,但是很守规矩,叫他找针,他就非常认真地低着头、弯着腰在足球场转。最后觉得实在找不着,他看见吃的,他也渴了,因为没有人请他,他也没去吃,他说“对不起,我没找着针”,他就走了。当然是打比方,生活中有这种人,很认真、很刻苦,但是没动脑子。
第二个进来的是法国人,法国人给人的感觉是很浪漫,叫他找针,他进来找了一圈,然后到旁边又吃又喝,然后抹抹嘴说我没找着,因为他认为找针这件事情没有意义。
第三个进来的是德国人,他当然说德国人强,德国人进来以后,叫他找针,他也看见吃的、喝的了,但是他没有马上找,他回过头来问游戏组织者,“我可不可以提问题?”这就是有思考了,我们经常不问。游戏组织者说“可以,我叫你找针,没有说不允许提问题”。他说“要求给我一根棍子”,你们想找针和棍子有关系吗?你们可能觉得没关系,但是其实是有关系的。拿了棍子之后他在球场上打格子,这就是磨刀不误砍柴工。不管是1米见方的格子还是两米见方的格子,人判断这个空间有没有针是能判断出来的,打格子可能花了四五个钟头,有吃有喝,找针累了又有吃有喝,最后肯定他能找到针。
雷曼教授讲完这个故事我想了半天,我们从小没有人这么教过,都是叫你聪明,要脑洞大开,要灵感,要去查资料,都是模仿,没有自己思考。所以当时我听了之后非常感动,我回到国内四处用这个方法,后来发现不灵。
1987年我再次到德国,我跟雷曼一块儿,我请他吃饭,坐下来以后,我突然说,第四个进去的是中国人,他当时没有理解,后来一下想明白了,他说“我很关心,中国人怎么找针?”
我说我们中国人进去跟你们一样,没有马上找,也是提问题,我们提的问题是“谁扔的针?是大力士还是小孩?是站在足球场的哪一点?朝什么方向?用什么动作扔的针?”问完我再看是要工具还是不要工具。
我讲完以后,我的老师大概有一分多钟没说话,他说中国人还是很有思辨能力的。大家想想我们真思辨吗?我们跟惯了,我们离开了拐杖,现在走不了了,我们改革开放、解放以后不都是靠引进吗?
所以今天的对话,我们要思考我们的设计教育,我们也是引进的,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我们引进了以后就躺在引进的这条路上走了,不知道自己再去认识了。我没有做过统计,但是有一个感觉,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或者解放以来,我们凡是引进的工业,基本停留在引进的水平上徘徊,因为有了拐杖,我们不思考了,跟着走就是了。但是凡是我们引进不了的,我们现在都可以拿到世界上跟人家比一比。什么原因?中国人不笨,中国人很聪明,因为有了压力,没有可模仿的,我们必须自己干。而我们的教育要培养这样的人,不能仅仅培养一个白领打工者。
这个问题,我觉得咱们的设计教育就要思考,你看我们一年毕业的设计类的学生,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数字,我一说给外国人,他们听了之后都很惊讶,我们一年毕业的设计类的学生,各个层次的一共有60万。我们这60万人都在做什么?都在最底层。
我们30周年设计教育,我们的设计学科的系统没搭出来,我们都在表现个人的能力、个人的聪明才智,都在挣钱,这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培养什么人才,什么叫人才?当然这个话又多了,展开又有很多话要说。


王受之:
我下面想问问柳老师,您从斯图加特三年访问学者结束了以后,又认得了雷曼教授,那您回到北京,按时间想应该是1984年。
柳冠中:1984年回来的。
王受之:
1984年回来之后,您就成立了工业设计系,我想请您给我们回忆一下,这个设计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当时有多少老师,开了一些什么课,为什么没有把雷曼教授那套东西完全植根到中央工艺美院,您回忆一下草创工业设计专业的过程。
柳冠中:
这又是一个很长的话题,1984年年初国内发了一个电报叫我赶紧回来,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叫我回来,反正很听话,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也没说什么事,就让我上课。因为我回来的时候没有接触到南方已经有构成课引进了,我就把德国学到的基础课拿来上。上的过程别的系,平面系也好,服装系也好,都在上构成,而我这里没有上构成,因为我没学构成,我就教我的整体的,从系统的认识设计。上的过程当中,反响就很大,我当时组织完第一次课之后就答辩,答辩是全校公开的,所以大家的反响很大。
王受之:那时候就叫工业设计系。
柳冠中:
那时候还没叫工业设计系,叫工业造型专业,到7月份放假的时候说要组建工业设计系,8月份正式成立,然后就任命我当系主任。后来从日本回来的一个教授当了副主任,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压力,整个7月份我就看了三本书,因为我要当系主任,我不知道怎么干,从小到大我的出身并不好,都是当一个乖学生、好孩子,从来没有当过干部的,不知道怎么干,我当时看了三本书,这三本书对我现在一直起作用。
王受之:还记得是哪三本书吗
柳冠中:
一个是《伟大的探索者爱因斯坦》,这是励志的书,这本书我全部都画了重点,他为事业不是为名、不是为利,而是探索、好奇。而我们现在是这样吗?咱们都是为了名、为了利,所以不可能坚持,这一点对我教育很深。
第二本书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是200年前瑞士的生物学家写的,他告诉我这个世界是系统的,离开系统的结构元素是毫无意义的,可是现在我们都在讲元素,就是不讲系统。这本书对我的教育意义很大,我为什么一开始就提出我的设计是系统设计,包括我的基础不是绘画、色彩、构成,而是设计的基本系统。设计不是孤立的,孤立讲美是造型,它是商业要用的,而设计不是追求这个。所以我们的设计教育问题很大,到现在我们还在追求表面的东西。
第三本书是在一个旧书摊上买的,解放军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关于人为事物的科学》,这是一个经济学家写的,得了诺贝尔奖的。
所以一上来我就把最关键的课给它改造了,就是我们把所谓的色彩课都去掉了,就上综合造型设计基础。任何造型必须受材料、工艺、技术或者是原理的制约,它的美是整合的,而当时正好参加国内有一个美学会,我就大谈设计美,不是形态美,不是技术美。当时提出技术美学,我觉得技术美学不对,技术本身没有美与丑,技术永远是工具,而解决问题,让人们感受到了反馈,这才是美,否则不叫美。而我们中国人往往把感官的东西当美,所以当时我就写了一篇论文,就是《共生美学》,讲的就是这个。
什么是美?悦目、悦耳的东西不一定美,它只是感官刺激,很新鲜,但是美不美不一定,也可能是丑,也可能觉得有病。你要今天这个场合穿了一件礼服进来,你说是美还是丑?你觉得有病,他在舞台上很美,但是在这个场合就不美了,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美是精准反馈,不是客观存在。客观存在只是高科技,更高、更快、更强,但是我们要不要更高、更快、更强?
所以我一开始就建立一个课程体系,当时建了几个课,一个设计概论,一个综合造型设计基础,还有一个是设计程序与方法,这三门课是重新建的,然后再谈人机学。当时我的课就不叫人机学,叫《人机学应用》,我们不是建立人机学的,我们是应用人机学。比如说你问我这个沙发舒服吗?人机学可以很舒服,但是我人是活的,我5分钟之后一动它就不舒服了。
所以我必须强调知识,知是静止的,识是运动的,绝对没有现成的人机学提供一个标准数据,你用这个数据就傻了,一定要研究人、研究行为,这是设计的本,而我们现在被技术、材料、装饰引导,这已经不是设计了,我们现在成天讲得好像很时髦,其实离设计还有相当一段距离。所以我们的创新,怎么理解新?比如说新材料,它对人不一定好,还有新药,它不一定治病,而是要对症,这就是一个适应性的行为,对你适宜,对我不见得适宜,这就是研究人,所以这个课题我们中国现在并没有真正解决。

王受之:
我下面的一个问题就是想问问你们的教学,我还是盯着那个历史的脉络来走,您回来以后,当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和广州美术学院,或者是无锡轻工业学院,其实主要的所谓的设计改革是改三大构成,而不是真正的设计系统,我身在其中,我知道这一点。中央工艺美院其实也有一帮人在改构成,并且他们用了很大的力量翻译了一些国外的书,您在改革的过程中,怎么处理这些老师之间的矛盾的问题?
柳冠中:
你要改革,要有新思想进去,就要讨论。当时工艺美院平面系都在上三大构成,而唯独我把三大构成取消了,只有综合造型设计。这样有的老师就不痛快,我就给他开讲座课,因为他们在讲座的过程中自己都承认,当时电脑都出现了,他说用电脑之后,三大构成没必要上了,它的变体比手绘多得多。
所以我当时跟老师们说,三大构成是艺术基础,而设计基础跟它不同在哪儿?艺术基础是不怕矛盾,设计基础要赢在矛盾上。我培养的是设计人才,我必须在矛盾中培养他,而不是理想状态中培养他,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到现在我们工业系也没有三大构成,别的系都有,只有我们工业系不上三大课程,我们学综合造型基础。
王受之:这个根源就在您这里。
柳冠中:
当时雷曼来了参观各个系,看哪个系上三大构成,然后别的系就介绍,这个构成课程是德国引进的,雷曼说,我没有这个构成课,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德国的包豪斯传到美国,美国传到日本,日本传到香港,香港传到内地,变成了三大构成。
实际上我认为三大构成并不是解决矛盾,而是讲究变化,变得越多越好。而设计的变化是受制于限制的,所以我们培养的就是限制项,就是戴着镣铐跳舞,不是想跳一个自由的街舞。所以工业设计难就难在它要解决问题,它是受限制的。
王受之:
当时我们的现代设计教育在中国的路径是三条,一条路径是江南大学的路径,因为他们有两位老师到日本留学,日本人的特点就是很容易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化,这是日本人的一个思维的方式,本来一个事情比如说在德国可能就是材料研究、综合基础,日本人把它分成若干项,把它分成了构成,还不止三大构成,后来还有光构成之类的东西,通过他们就到了江南,所以在华东很流行。
第二是这一派思想到了日本,日本到了台湾,在台湾翻译完了之后到了香港,然后香港的一群设计师,包括靳埭强先生就把这本书带到广州美院,所以广州美院也在大搞构成,并且把构成和现代设计打了一个等号,搞构成就是做设计,不搞构成就是不做设计,你是构成派还是传统派,好像就变成这样。我去广美的时候就遇到这种情况。中央工艺美院的情况就比较好,因为柳老师从德国一口气回来,就没有成立这个三大构成,所以一口气就成立了设计的系统。
柳冠中:在学校里受排挤,很难。当然我在这里说就不太好,当时我是差一点挨批判了。
王受之:就是没基础课。
柳冠中:
当时史论系组织了一个题目论工艺美术前途。有一个老师让我来发言,当时讲了工业设计,没想到讲完之后,第二个发言就是批工业设计,批柳冠中,第三个又是这样,亏得史论系的老主任站起来了,他不知道背后的组织,他说今天我们议的是工艺美术前途,干吗要批工业设计?这一句话就把这个批斗会打散了。
大家知道我出的第一本书,不是出版物,是《设计文化论》,在党委叫黑皮书,因为它的封面是黑的。当时跟中央电视台拍的录像片《设计的文明》,动乱开始之后,所有的节目都停了,中央四个台反复播这个,因为这个节目在之前我交给党委审查了,党委说不行,不能发表。但中央电视台不管,把它发了。结果后来播了一个月,每天都是讲那个,谈我们中国往哪儿去,设计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我们想的工业美术的延长、工艺美院的一颗新芽,不是这么回事,这是两种观念,一个是手工艺的社会,一个是工业社会,它的经济基础不一样,生产关系不一样,现在这个问题仍然没解决,现在我们仍然是在手工艺的思想基础上搞设计。所以设计教育在中国,我觉得任重而道远。
王受之:
我现在还想问一个比较个人的问题,您可以选择不答,但是我还是希望您能答,因为你们两位筹建工业设计专业的另外一位王明旨老师是日本留学回来的,我就想了解您和王老师所受的教育思想有没有相似的地方?有没有不同的地方?其实我的好奇是在于想知道日本和德国的教育有没有差异?
柳冠中:
应该说从工业设计的角度,日本的水平和发展中的我们基本上是在正常健康的道路上,所以我们俩一块儿搭配的时候,概念基本上是一致的,没有什么分歧。当然我是系主任,可能我的意见更强一些,而且我这个人口气上比较强势,王老师比较内涵,他不一定完全赞同,但是基本上比较融洽。
但是后来由于各种关系,王老师当了副院长了,可能是从全面的角度,因为是工艺美院,不光是工业设计学院,他要关照到其它的学科,不能迈的步子太大,所以从工艺美术全局的角度,他有他的一些主张,自然就会有些区别。应该说我们在合作期间还是很愉快的。毕竟是现代设计,日本也是讲的现代设计,所以没有什么分歧。


王受之:
下面我想了解一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到了2000年以后,你们的工业设计教育,您在位上和王明旨老师在位上,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重大教育改革的步伐和成就?因为我们在外面不是很清楚,所以想请您讲讲,工艺美院取得了什么成就?
柳冠中:
这一点的确我是一直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在工艺美院得到了很多的熏陶,它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它把艺术、设计和工艺结合在了一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温床。我们并到清华之后就有一些变化,所以大家对工艺美院进清华褒贬不一。
冷静来看,工艺美院进清华这件事从长远来看绝对是对的,因为未来的世界绝对不仅仅是工艺的设计,它应该是综合的,进了清华之后有了其它的学科背景,它的发展的道路应该会更开阔,但是这个结合过程很痛苦,很漫长。
我们并到清华之后,当时清华的校长王大中组织我们教授以上的人座谈,他当时的讲话对我的触动很大。他说清华培养的人才是特殊优秀人才,绝对不是培养小作坊主的,希望工艺美院进来之后不要仅仅在自己的小领域中称王称霸,你要在整个社会上起到影响作用。也就是放到一个社会的平台上检验,而不仅仅是局限在一个小学科里。他希望我们工艺美院从清华出来的人,应该是引领这各专业发展的,而不是跟随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进了清华之后,我们工艺美院和清华的文化差别不大了,到现在我们分不出清华和工艺美院的学生。当时有一个笑话,我们刚合并的时候,大课还要到清华校园上,清华的学生到了大教室一拉过来,清华的学生看我们像看展览一样的,因为大家的穿着打扮全不一样,上完课出来,好多理工科的老师拿着花在等咱们工艺美院的学生出来。现在没有这个区别了。
王受之:
融为一体了。我记得当时《中国青年报》登了一篇文章,就是中央工艺美院合并到清华大学,变成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说到中央工艺美院学生在清华园的特殊的情况,就是这帮人的奇装异服,一道风景线,长头发、男不男女不女,最强项是把清华仅有的几个美丽的女生堵到厕所不敢出来。
这是说他们的,这是他们刚合并的时候看到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现在过去看不见这种情况了,觉得都像清华的人了,融入了那个学校,那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王受之:
讲到这里,关于学院的话题就要告一段落了。等一下我们要开放一个提问的环节,大家说王老师你怎么老在问柳老师,你自己不讲?因为我是当主持的,我是个托儿,今天主要是柳老师讲,如果你们想要我讲,你们等下提问题,我可以回答。
我接下来想问问柳老师,中国现在的工业产品设计走到目前这个阶段,我们有什么可以总结的成就?因为柳老师最熟悉中国的工业产品设计,有什么真正是很要命的问题?特别是我们怎么能够完成从“中国制造”变成“中国设计”。这个过渡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有些问题我们解决不了,也有很多问题我们如果了解,应该是能解决的,特别是通过教育解决,所以请柳老师给我们讲讲中国的工业设计现在的情况。
柳冠中:王老师又问了一个大话题,我又有很多话要说。时间不能占用太多,但是必须说。
王受之:有足够的时间,现在才3点半。
柳冠中:
中国工业设计教育,刚才王老师说了工业设计产品,其实我的看法是工业设计,我们叫工业设计,艺术学院叫工业产品设计,我觉得这是把中国的工业设计拉回了20年,倒退了20年。
王受之:
据说有几个科学院的院士还是工程院的院士开会,谈到了工业设计这几个字,然后就说了一句“工业设计那怎么能是他们搞美术的人做的呢?当然是我们搞计算机,搞机械的人设计的”,就强行把名字拿走了。
柳冠中:
而且不光拿走了,还说工业设计是1.0,说现在的创新设计是2.0。这很荒唐,技术有1.0、2.0,当我有了2.0之后,1.0就扔掉了,设计能扔吗?所以这就是误解,把技术等同于设计,技术创新就等于设计创新,这是中国现在最大的一个误会。
我们技术是引进的,我们可以一下子有了。我们解放前没工业,我们解放后引进,改革开放之后又引进40年,国外有的东西,我们基本上都有了,但是我们引进的东西徘徊在引进的水平上,知其然没有知其所以然。
我们说的“中国制造”,“制”是我们的吗?不是的,是引进的,我们只是“造”了。廉价劳动力、污染的不自觉,材料浪费的不明白。所以中国没有完成中国制造,我们是加工型的制造,在这样一个体系工业基础上,我们要的设计是什么?是外观。所以我讲得不客气,咱们工业设计发展这么热,大家想想目前中国设计的主体在哪里?设计公司。咱们深圳有多少设计公司我不知道。
王受之: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反正很多。
柳冠中:
咱们的设计公司是接单式的。你接单多长时间?三个月、三个礼拜,5万块钱。你想5万块钱,三个月的工作,能做什么设计?不就是外观吗?所以中国的加工制造业决定了我们的工业设计这30多年基本上是做外观的,你不愿意做也不行,因为你为了拿到尾款,必须听老板的,所以我们就是解决表面问题的。
中国的设计和欧洲不一样,欧洲的社会是工业化了的,它的设计公司起到了非常积极主动的作用,因为它的设计公司接的单不是一般的生产服务业,他是主动的,我们是服务业,我们是听客户的。
所以我们的设计是打游击,但是都有体会,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我去创业,一个电脑就可以接单,几个人能做什么设计?你只能做表面。
所以这些决定了中国的工业设计基本上在这个阶段,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从美工到有设计师,这应该是伟大的进步,过去我们不愿意听,我们叫美工,现在我们叫设计师,等于说我们有了做设计的兵了,能打仗了,但是我们打的什么仗?游击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今天接这个单,下个礼拜接那个单,只要能活下去就行,小日子过得都还可以。
当然最近这十年来开始变化,因为我们一直在宣传工业设计的主战场不是工业设计公司,我觉得咱们深圳要思考,深圳的工业设计是很厉害的,你们一定要进入企业,企业是主战场。
你进入企业就马上发现,你这个冷兵器不管用了,你要打阵地战,要建工事,要有机枪阵地,要派出侦察兵,你甚至还要有狙击手,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工业设计师对你的要求不是一个造型,你必须了解市场,了解需求,了解工艺、了解结构,这样设计师的能力就在提升,它往横向扩展了,而不仅仅是你的效果图、渲染。你的能力扩展了,这才是设计的本,设计是综合能力的解决方案。也要让企业了解,设计不是一个造型,而是从头到尾的了解,设计是全程干预的,这是第二阶段,我们叫阵地战,中国现在开始有百分之一二的公司在做这个了,当然深圳也有,广州也有,江南相对更多。
王受之:江浙一带?
柳冠中:
对,因为他们起步晚。包括郑州,它在5年前开始,设计公司一上来就是给企业整体服务,而不仅仅是接单,它一上来就跟企业深度合作,他也做短期的活,但是他必须三五年拿出一个根本的产品发展计划,所以他们开始全面思考,这是中国进入第二阶段。所以中国的工业设计现在面临着我们能不能把主力放到主战场的局面,这才是解决“中国制造”的“制”是我们的,而不是“造”,“造”是关注外观,“制”是关注原理、新理念、新体系,这样才有新物种,不是变一个造型、加一个功能。
王受之:
这个说法大家记住,“制造”的“制”我们还没有,我们现在其实是“造”,我们要把制造做好,其实是要把“制”做好,这是柳老师的观点。
柳冠中:
我们的学习也是,我们关心在社会上很多小公司,所以很多学校改革,强调建工作室。这一点我的观点跟大家又不一样,艺术院校可以搞工作室,设计学校千万不要搞工作室,一搞工作室,你就是小作坊了。
工艺美院原来没有工作室,都是整体学校给社会服务。现在进了清华以后,因为有了艺术家,就搞工作室,美术家一搞工作室,设计师也要搞工作室,一搞工作室,就是三三两两的。我的同事在工艺美院原来是三两天都要碰到的,现在三两个月不碰面都很正常的,都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接单,别人的工作室我们都不能进去了。大家没有沟通了,这个学校被斩开了,都是小工作室,小日子过得都非常好,但是整体力量萎缩了。
而设计的力量就是要整合,包括制造也是。我们都是小微企业、中小企业,这些企业怎么办?10年前汪洋在广东讲转型升级,底下企业家交头接耳,今天转今天死,明天转明天死,慢慢转慢慢死,我当然慢慢转。所以转型不容易,不是今天我做麦克风,明天做机器人,那是转生产,不是转型。转型是体系转,不是光改一个工作对象的问题。所以这牵扯到设计到底是什么,咱们对这个认识还停留在比较浅的层次,它不光是一个造型,不是一个表面的东西,不是生产的产品。所以现在国内很多设计公司在转,它已经开始认识到必须跟产业结合,它才有后劲,才能做研究,否则研究不了,没人支撑他。
王受之:
现在各个美术学院都在搞工作室,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摧残。我在广州美院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开公司,这样还不错,开公司因为够大,起码有几十个人,包括有集美组这种大公司。到后来搞工作室,现在工作室越搞越多,就变成了农民的小作坊,所以走到大学里面去你根本就找不到人,因为每个人就躲在自己分的那两间房,带着几个研究生做项目,有商业机密,所以学校的研究力量基本上就化解了。
我说现在要改造我们的设计学院,除了课程改革以外,很大的一点就是要把这些工作室都封掉,要成立就用整个学校的能力去做大的公司,工作室真的是把学校完全化整为零,把它瓦解了。
柳冠中:
王老师说得非常正确,但是一旦分了工作室之后,要把它整合太难了,分开以后要收拢是要流血的,所以一旦分了要合,你得找时机,你得找社会的综合项目来合,否则你单纯的合凭什么?我跟你玩命都可以,我挣钱的小买卖被你砸了,所以这就牵扯到我们怎么理解设计教育的实践。
我这里又有话说了,我们现在的实践多数是小公司,或者是工艺美术的作坊,作坊就是一个师傅带着几个徒弟从头做到尾。所以有一句话叫随机应变,这就是小聪明,比如说我一个石头刻出了一个瑕疵,随机应变把瑕疵变成小甲壳虫,这是小聪明,这是工作坊的实践。而我们理工科的实践是实验室,实验室是实践什么?是探索,是试错,是颠覆。而我们学设计的,很少有这样的工作坊或者实践。
还有一个是社会实践,就是我要跟搞教育的合作,我要跟搞工科的合作,我要跟政府官员合作,我要跟企业家合作,这个实践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不是专业实践,而是社会实践,咱们这个学校将来要培养的就不是简单的设计师,而是要培养产品经理、设计总监,他的职责不仅仅是设计,而是恰恰对别的学科的了解,能够指挥、整合别的学科的,这是我们现在最缺的人才。
所以现在企业里面搞产品总监的有学外语的,他跟外国人接触,学管理的做设计管理,真正学设计的做设计管理的很少,因为他只是打工仔,听别人的意见,叫你改造型你就改,你站得不高,你要站得高就必须站在设计之外,他能够统辖、指挥设计工作者。这是中国最缺的,中国不缺设计师。
王受之:
柳老师提出这个关于设计教育的方向性的问题,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我估计也是在国内比较少的在公众论坛上提到的,就是设计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一班技术熟练的设计师,那是职业学校的事情,真正应该培养的是设计管理的人才,因为这种人才是能够统领其他的内容,并且知道怎么服务于社会,这是一个核心。如果我们不从这个角度想,我们的教育的整个的运作其实是培养职业学院的学生,就是熟练的技能人才。
柳冠中:培养加工制造业所需要的人才。
王受之:
这一点今天我受益匪浅。听到这一点,我觉得这个事情可真是闹大了,如果我们要做得好,我们怎么样能够给他们这方面的能力?
下面我就接着这个问题问柳老师一点,您觉得我们一个好的设计师要能够很好地去管理其他的行业各个方面,他应该具有哪些素质?人文素质是肯定的,还有些什么素质您认为是我们在教育里面可以教育的呢?
柳冠中:
这又是一个关键问题,我们这四年学什么?因为设计是一个综合学科,我学人机学四年,学材料学四年,学机械学四年,学艺术学四年,我还干活不干活?所以设计教育的特点就是,它恰恰不能这么单科独进的学,它需要整合的学,在一个项目整合的过程中,把各种知识穿插过来。在这个过程中,他学会自己去扩展知识,所以咱们的设计教育培养人才,首先要学会他自己找知识。因为他要跟别的学科合作,他要跟别人交流、沟通,要别人听他的,他必须是要给别人沟通,你沟通的时候一问三不知,人家根本就不理你了。你说结构,你连结构的概念都不知道,他不可能跟你交流,所以学设计是一辈子要学的,你要跟结构沟通,你首先对这个结构事先要预习,你要达到一个基本的水准才能跟他对话。
王受之:不能依靠教室里面教你的知识,一定要学会自己找知识。
柳冠中:
可能有人说我这样是把设计说得高了,其实不是。说得高是我们培养导演、指挥,说得俗一点,我们是培养大师傅。大师傅不会种水稻、不会养猪,不会做煤气灶,但是他能炒一手好菜,说明他的综合能力,他知道什么样的米做什么样的饭,什么样的菜怎么炒,什么样的煤气灶用什么样的火候,所以设计师要有这个能力,他才能跟不同专业的人去合作。这个沟通能力跟理解能力要非常强,他必须是一个杂家,他能判断出这个米不适合做这个饭,这个米要焖多长,用多少水,我们要具备这个能力,我们才能跟技术专家、心理学家去讨论,让我的看法他能支撑,能使我们的看法落地。
王受之:能够自己主动地去学习知识。
柳冠中:
我们培养的目标一定不是追求100分,这是给家长看的,给你自己安慰自己的,而真正是在这个课程当中,你自己学到了多少能力,这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句话,我教你打猎,不给你鸡鸭鱼肉,但是大家关心的还是鸡鸭鱼肉。教你打猎就是我到任何场合我都能打到吃的,没有羊,我可以抓鱼,没有鱼,我可以采果实,这是适应能力,适应能力就是你必须要善于跟别人沟通。而在生活当中,处处是知识,所以设计师最重要的一点是生活,生活中的道理都是非常简单的,没有那么复杂,你再一追问,它的原理也就那些,没有什么看不透的东西,所以必须要善于生活。
王受之:善于学习知识,自己独立找,善于生活,具有生活的能力。
柳冠中:
而且要多问为什么,千万不要看《十万个为什么》,你看完十万个为什么,答案有了,你就不探索了。所以你跟外国人讲,中国人喜欢看《十万个为什么》,外国教授就不理解,你看这个干什么?你看了结果,你就不探索了,恰恰我们都要来反问“是吗”?要怀疑,要提问题,你才能有所创建。


王受之:
我下面一个问题是问问柳老师自己,因为柳老师是我们这代人当中最有魅力的一个老师,中央工艺美院和清华美院所有的人都说这是一个大帅哥,从年轻到现在都非常帅,又很能说话,大家都很喜欢他,并且他很有领导的感染力,他一出来,这个场子基本上就镇得住。所以我就想问柳老师,这也是一个能力,您这个能力是从小就有的呢,还是后来慢慢自己自觉地培养的?就是能够把场子镇住,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都听您的,您这个个人魅力是怎么形成的?
柳冠中:这个说起来惭愧,我从小是一个乖孩子,很听话的,因为从小因为出身问题,只能老老实实上学。
王受之:夹着尾巴做人。
柳冠中:从来不善于表达,我答卷都怕,一提问题一个大红脸,什么都说不出来。
王受之:到大学也是这样?
柳冠中:
就是“四清”的时候,1963、64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到农村,在河北邢台,那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地方,我去了一个小村,这个小村一共是七十多户人家,三个工作队,一个老干部,有一个其它公社的社长,还有我们这些大学生,还有一个当地的农民小知识分子。进到村里面,要抓革命、促生产,白天带着农民下地干活,晚上做查帐、四清,或者是调动发动群众。
到那里第一个礼拜以后,老干部走了,就剩下我跟那个小年轻两个人,要领导农民干活,我是在上海长大的,农村里干什么活我根本不知道,这个生产队的地块在哪里都不知道,我怎么敲钟派活?因为所有的队长都靠边站了,你得领导下地,你怎么给他们派活?这10个壮劳力往哪里派,哪些有技术的往哪里派?你必须要请教,头一天就要了解村里的情况。然后晚上要开批斗会,要访贫问苦,逼着你这么做,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必须要给农民讲23条,必须讲四清,你不会讲硬着头皮都要讲,我骑自行车都是在那时候学会的,因为一个礼拜就要到公社去汇报,汇报的路很长,我走过去根本来不及,就是借一辆车,一路摔跤摔到公社,回来的时候就会了。所以就是亲自实践,就是现场锻炼。
1984年我回到学校上课,我刚开始也是不行,最开始上课的时候,我准备了一天,40分钟讲完了,最后不知道讲什么了,因为我做的准备都讲了,所以实际上是锻炼出来的,本来不会说话,一上台就脸红的,现在就是王老师说的,我上台可以侃侃而谈,讲一天、三天、五天都没问题,就是克服了心理的障碍,这是第一个,你必须要讲,你不讲不行。第二,你首先得有自信。第三,你必须要了解设计之外的东西。所以现在我能讲,不是因为我口才好,从小口才不行,但是现在肚子里有东西,我能表达出来,有很多东西要说,我急于表达,这是自然出来的,刹车都刹不住。
王受之:像柳老师这样有魅力的老师在我们设计界没有几个。柳老师是最高级的那个。
柳冠中:王老师也是其中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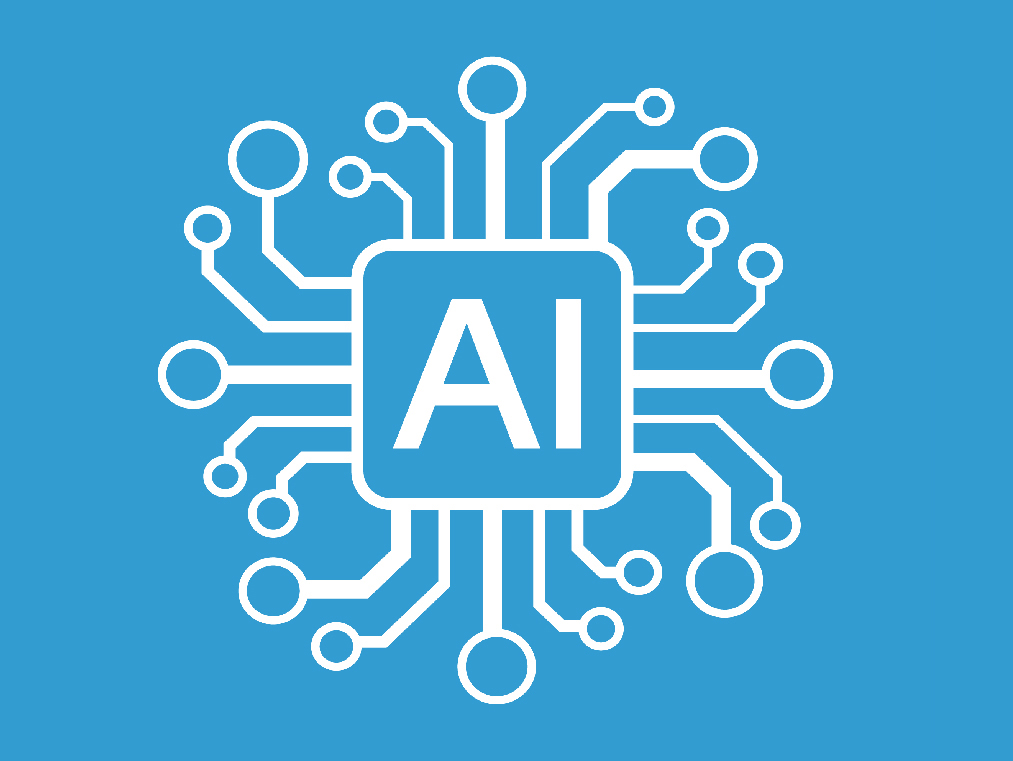

沃路得转变——巴斯夫推出《2023-2024汽车色彩趋势报告》
2023-09-27
